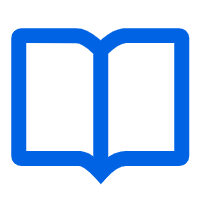繆属五行属什么?
“繆”字的五行属性到底是什么呢? 《康熙字典》中,“繆”字解释如下: 《字汇补》云:“缪,姓也。”引明·朱国祯《涌幢小品·卷二四·仇大娘》:“缪氏,世居金陵(今南京),为世族。”“缪”字又解作姓氏用。 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均收录的异体字“繆”的解释却是: “繆”是“缭”的字形错乱而来。《集韵》里“繆”字条下引用唐代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的话来注释这个字:“繆本亦作缭。”可见这个“繆”字原本指的就是“缭”。而《汉书·张骞传》中有“缭以木,其状若楼”一句,说的正是“繚”字的意思——绕、缠。 《广雅·释丘》:“繚,曲也。”王念孙疏证:“繞者,帀也;繚者,曲也……二者皆是回环往复之义。”
综上,“繆”字最初的字形应该是像打了个结似的“繚”字。而这个文字最初表示的意思是缠绕,也就是五行所属为火。 但是后来这个字被误认为“穆”的变形字,被用来姓和名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它变成了个“俗字”——被广泛使用的字。于是,在宋元时期的几个重要文字资料里,比如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等书中,都把它收归一类,并统一给了“穆”字。这样,“繆”字的五行属性就被改成了水。
那这个改动的根据是什么呢?据我观察,可能是基于下面这一点:“穆”和“繆”这两个字在古代汉语中经常互相通用,而通假字往往是用来表示同音字或者形近字的。那么,它们既然能代替对方,就说明它们的五行属性也一样。而“穆”字从金,五行应属土;“繆”从火,五行应属火。而土能和火相生,所以把“謬”改成五行属火的“穆”显然是合理的。 当然,这种改动的依据并不是正式文献里的记载,而是后世学者自己总结发现的一个规律而已。 不过,虽然“繆”字从火改为从水的转变过程有上述根据,但“繆”字本身是个古字却是不假的。古文字学者们通过研究金文的形状给这个字确定了本字,并且它确实属于一个最早见于商代早期的文字。
缪姓在繁体字中,是“缪”,念mào。该字在《康熙字典》等旧字典中,归入了“系”部。《说文》:“系,维也。”“维,车盖衣总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总者,束也。维之本义当训为会束。”这样,“系”字就应以“维”、“会”、“束”等字的本义的属性为自己的属性。
“系”字从糸,表示与丝织品有关。从“糸”字,可以联溯到它的原古文字。它的原初表意是一个正在缫丝者的形象。甲骨文(又见于金文和篆文)、金文、篆文的“糸”字,其字形就是一个人坐在“田”字形的装置上,两手正在缫理丝茧,如甲骨文左边的字形。右边的甲骨文,上面的部件就是“茧”字,下部的构件字是“田”。
该字的构件“茧”字,它的原初字意是人坐在“田”字形的养蚕、缫丝器具上,两手正忙碌地张罗。《说文》:“茧,蚕茧也。从系、从贝。象形。凡茧之属皆从茧。”段玉裁注:“蚕作茧,如人之为维束,故从系从贝。贝壳至坚牢,而丝得之以为维束,故系、贝兼取以为茧。”该字的字意与前面所讲的“糸”字有关且相象。“系”字、“茧”字都是从“田”,“田”字像人坐形,表人坐于养蚕场(蚕房)上正经营织作蚕茧。“贝”的本象就是贝壳,借指坚硬之物。两字的本义也与“贝”有关联,就是蚕茧硬壳类的结块事物的象形。
“繆(缪)”字本义与“系”字、“茧”字相同。“繆(缪)”字,其甲骨文字形,表示人卧蚕茧上。金文、篆文字形与“茧”字形相同。《说文》:“繆(缪),绞丝也。从糸,矛声。”段玉裁注:“绞丝,合丝以强之也。即今之纽丝,纽、绞音义同。”又:“今之用丝之字,与纽絿义相类者五:一曰纽,如纽络、纽丝之类;二曰纽,如纽回(扭、揉)之类;三曰纽,如纽屈之类;四曰絿,如絿约之类……纽之引申为缠、为纽、为拘、为缠绵不绝,与纠之引申为纠缠,为纠牵,一也,此盖织事所最亟也。”“缪”的本字就是“繆”,“缪”是“繆”的简化字,也读miù。这是另一字,有谬误、欺骗等义。
“缪”的“纽丝”本义已隐性地反映在“缪”字的字形中。“缪”字的“纟”旁,就是“繆(缪)”字的构字部件,也表示本字与丝织品有关。这个字,字典、辞书一般都归入“纟”部。“纟”部是一个“会意字”由“糸”(原字写作“丝”)和“丿”合成,整个字形象一个人(下部)将丝(上部)绞在一起。“缪”字的“纟”旁原字本义、字意、字形特征,说明了“缪”字与“矛”(纽)丝有关,就是缫丝、缠丝、结丝之事。
人之所以要缫丝、缠丝、结丝,目的在于使丝牢固,结实、坚硬。这样“繆(缪)”字应以“系”、“维”、“结”、“牢固”、“坚硬”等字的义蕴为自己的属性。“繆(缪)”字从矛(纽)声。“矛”的甲骨文字形,“木”字像木把,上部像是“冒”字的“声符”,字从“冒”。《说文》:“冒,覆也。”“冒”字原从巾从出,像巾着其首而覆着之形。“冒”字应以“巾”字“巾”部的属性为自己的属性。“